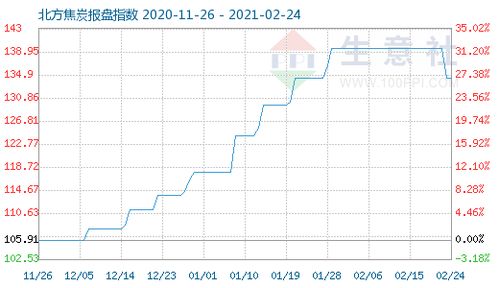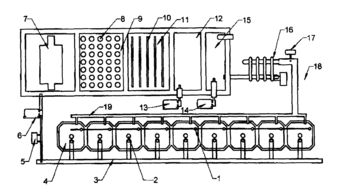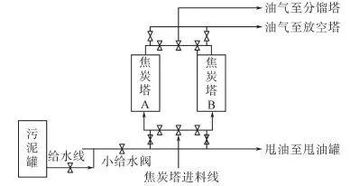深夜,城郊工業(yè)園區(qū)的一角仍彌漫著刺鼻的焦糊味。火光雖已熄滅,但廢墟上蒸騰著縷縷青煙,如同一聲沉重而無(wú)聲的嘆息。眼前,曾堆滿五顏六色、質(zhì)地各異的布料的倉(cāng)庫(kù),如今只剩下一片黢黑的斷壁殘?jiān)约岸逊e如山的、蜷曲碳化的布匹殘骸。服裝廠老板李建國(guó)站在警戒線外,一動(dòng)不動(dòng),仿佛也成了一尊被煙熏火燎過(guò)的塑像。他手里緊緊攥著一小塊僥幸未被完全吞噬的布片——那本是下一季主打款的雪紡面料,如今已焦脆如枯葉,輕輕一捻,便化作簌簌黑屑,從他顫抖的指間飄散。
這場(chǎng)起因于電路老化的火災(zāi),燒掉的遠(yuǎn)不止是這近萬(wàn)米、價(jià)值數(shù)百萬(wàn)的布料。它燒毀的是李建國(guó)半生的心血,是全廠百余名員工下個(gè)月的生計(jì),更是數(shù)十個(gè)已簽訂單所代表的信譽(yù)與未來(lái)。這些面料,是他跑遍江浙滬紡織市場(chǎng),精心挑選、比對(duì)、押上全部流動(dòng)資金才購(gòu)回的“戰(zhàn)備糧”。其中有為高端客戶準(zhǔn)備的進(jìn)口真絲,有年輕人喜愛的環(huán)保再生纖維,還有大量基礎(chǔ)但至關(guān)重要的棉布與滌綸。如今,它們不分貴賤,統(tǒng)統(tǒng)在烈焰中歸于平等的灰燼。
“完了,全完了……”這是火災(zāi)后李建國(guó)說(shuō)得最多的一句話,聲音干澀得如同砂紙摩擦。他愁到極點(diǎn),眉頭鎖成的“川”字仿佛用刀刻上去的。這“愁”,是具象而尖銳的疼痛。他愁眼前:原料盡毀,生產(chǎn)線即刻斷供,如潮的訂單交期迫在眉睫,天價(jià)的違約金單據(jù)仿佛已雪花般飛來(lái)。他愁背后:工人的工資、銀行的貸款、供應(yīng)商的尾款,每一筆都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脊梁上。倉(cāng)庫(kù)的保險(xiǎn)因年初資金緊張未能續(xù)足,此刻更是雪上加霜。他更愁未來(lái):商海浮沉二十年,從縫紉機(jī)作坊做到如今規(guī)模,信譽(yù)是他最珍貴的資產(chǎn)。此番變故,客戶信任一旦崩塌,重建之路何其漫漫。
這場(chǎng)“煤”(火災(zāi)的災(zāi)禍)來(lái)得猝不及防,卻并非無(wú)跡可尋。事后反思,老舊廠區(qū)的電路隱患、為節(jié)約成本而略顯擁擠的倉(cāng)儲(chǔ)布局、也許存在疏漏的夜間巡查……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被日常忙碌所掩蓋的細(xì)節(jié),在災(zāi)難的放大鏡下,成了錐心的悔恨。李建國(guó)此刻的“愁”,已不僅僅是經(jīng)濟(jì)損失的焦慮,更夾雜著深深的自責(zé)與無(wú)力。他望著廢墟,眼中映出的不只是焦炭,更是無(wú)數(shù)家庭期待的目光,是他自己從青春到中年在這行當(dāng)里留下的每一個(gè)腳印,它們似乎也都在火光中變得模糊。
絕境之中,微光亦在萌動(dòng)。火災(zāi)次日,園區(qū)管委會(huì)牽頭召開了協(xié)調(diào)會(huì),商討幫扶措施。幾位多年合作的客戶得知情況后,主動(dòng)打來(lái)電話,表示可以酌情延長(zhǎng)交貨期。廠里的老師傅和工友們沒有一哄而散,反而默默回到尚未受波及的車間,整理殘存的小批量輔料,檢修設(shè)備。“老板,只要廠子還在,機(jī)器還能轉(zhuǎn),我們就能從頭再來(lái)。”老裁剪工的一句話,讓李建國(guó)熬紅了的眼眶第一次有了濕意。
從“愁到極點(diǎn)”到“重振旗鼓”,中間隔著一條名為“廢墟”的鴻溝。李建國(guó)知道,他需要面對(duì)的,是繁瑣的災(zāi)后評(píng)估、是艱難的資金籌措、是重織供應(yīng)鏈的漫漫征途。這個(gè)冬天格外寒冷,但或許,這片被火燒過(guò)的土地,來(lái)年能孕育出更堅(jiān)韌的芽。他彎下腰,從灰燼中拾起一顆被燒得變形的金屬紐扣,緊緊握在手心。那不再是柔軟的布料,卻有了另一種堅(jiān)硬的質(zhì)感。前方萬(wàn)難,步履維艱,但站在這片焦土之上,他除了選擇在灰燼中重建,已無(wú)路可退。這場(chǎng)“煤”,燒光了他的庫(kù)存,卻也淬煉著他和這個(gè)企業(yè)的脊梁。長(zhǎng)夜未盡,但東方天際,已隱隱透出一絲微白。